捕后判决轻刑率偏高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批捕案件质量有缺陷,另一方面说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落实不到位,制约着侦查监督工作的发展。笔者以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郊区院)办理的捕后判轻刑案件为研究对象,对捕后判轻刑案件进行原因探析,以改变捕后判决轻刑率高的问题,提高诉讼监督工作质量。
一、捕后法院判轻刑案件的特点
2013年,南郊区院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178人,经审查,批捕150人,不批捕28人。在批捕案件中,判处轻刑34人,轻刑率22.7%,所占比例高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考评标准值7.7个百分点(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考评标准值为15%),[1]呈现以下特点:
1.从判决结果看,捕后判轻刑案件刑种均为拘役刑。其中,单处拘役刑5人,拘役并处罚金刑29人;拘役刑期最低2个月,最高6个月。
2.从判决罪名和案件类型看,多为盗窃(数额较小)、寻衅滋事(情节非特别严重)、诈骗和故意伤害(轻伤)等轻微刑事案件。盗窃案判轻刑人数占78.9%,寻衅滋事案判轻刑人数占21%。盗窃案22人中,犯罪数额从最低的1000元到2950元,其中,在“两高”及山西省“两院”关于盗窃数额标准确定前,[2]接近犯罪起点的有6人,确定后,接近起点的有17人。法院判决时,从轻处罚依据均为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引用了《刑法》第67条第3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规定。
3.捕后判轻刑的案件存在以罚代刑倾向。捕后判轻刑中并处或单处罚金31人,占判轻刑总人数的91.1%,但据法院具体执行罚金的实践来看,罚金执行效果不如人意,罚金刑在逐步变为缓解主刑的一种判决宣示,甚至成为抵顶主刑的附属而失去其本来意义。
4.捕后判轻刑案件在逮捕前全部采用拘留措施,对犯罪嫌疑人持续羁押,在一些犯罪嫌疑人具有两项以上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时,仍然被逮捕羁押。
5.捕后判轻刑在捕后因证据发生变化的有12人,盗窃退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7人,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的5人。
二、捕后法院判轻刑的原因
捕后判轻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规定、执法体制上的不完善等客观原因,也有办案人员执法理念、公众认识偏差等主观原因。主要表现为:
(一)办案人员的执法理念陈旧
受传统执法观念的影响,办案人员的执法理念没有彻底转变,存在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配合协作、轻监督制约的思想,批捕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构罪即捕”的观念,没有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新的司法理念贯彻到批捕工作中。虽然《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对“有逮捕必要”和“无逮捕必要”的情形作了详细列举,但这一规定是检察机关的内部规定,对公安机关没有拘束力。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只注重审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及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忽视了对“有逮捕必要”证据的收集,以致造成批捕率高、捕后轻刑率高。虽然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在报捕案件的同时,另行报送“逮捕必要性说明书”,但公安机关并不加以具体分析,只是将法律规定逮捕必要性的条文附上报送,使得这一诉讼活动流于形式,公安机关看中的是破案率、逮捕率,两部门在执法理念上存有大的差距。根据我国《刑法》,缓刑的适用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与批捕犯罪嫌疑人时衡量是否“不致发生人身危险性”所参照的各种因素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批捕后判缓刑居高不下的现象,反映出在审查批捕阶段办案人员执法观念保守、逮捕条件掌握失当。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白某于2013年1月22日凌晨到一宾馆员工宿舍盗得手机4部及现金510元,经鉴定被盗手机价值520元,案发后已发还,法院作出了对白某拘役4个月的判决。在当时,该案盗窃数额刚刚达到犯罪起点,依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之规定,在3个月拘役至6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为量刑起点。虽然白某自愿认罪、退赃,但因其是外地人而予以批准逮捕。
(二)受执法环境的影响,办案人员对诉讼风险的把握较为谨慎
一方面,由于相关机制不健全,地方党委、政府乃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会影响执法办案,办案人员对未剥夺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是否会逃跑、毁灭证据、躲避审判等妨害诉讼的行为无法确定,对不捕风险顾虑重重,存在怕担责任的想法:怕不能保证诉讼被指责打击不力;怕领导和上级机关质询;怕公安机关不理解;怕当事人质疑办人情案、关系案;怕被害人上访承担影响稳定的责任。因而从防范风险的角度考虑,在构罪的前提下首选逮捕,由此导致逮捕措施适用率偏高。另一方面,对一部分明知其犯罪行为可能判轻刑的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为外来人员,或有犯罪前科,或有吸毒被强制戒毒、赌博等劣迹,或为流窜作案、无固定住所人员或监护人的监管不力等因素,对其若不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可能导致诉讼程序中断,无法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增加诉讼风险,只能批准逮捕。另外,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在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情况下,虽预计已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轻刑,但为防止其与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之间有串供等妨害作证的行为,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对此类犯罪嫌疑人也多采取逮捕措施。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陈某系社会无业人员,无固定住所,1996年因盗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刑满出狱后又5次因吸毒被劳动教养。为筹措毒资,陈某盘踞在当地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对过往的顾客、商户扒窃,明目张胆犯罪,群众对其深恶痛绝,案发当时,其已得手两次,后被被害人和巡逻民警发现抓获。据此,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但法院在认定陈某有前科劣迹酌情从重处罚后,判决陈某拘役5个月。 类似案例二中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其价值在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在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前提下,作为审查逮捕部门和案件承办人,应当重点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即逮捕的必要性,对于类似案例二中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应当予以逮捕。
(三)社会公众对逮捕的认识存在误区
一些社会公众把逮捕措施看作是一种预期刑罚,是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宣告,而不是从一种诉讼保障手段的本义去认识。在双方积怨较深、矛盾尖锐的轻伤害案中,不捕决定常会引发被害方的强烈不满,进而上访闹事,影响社会稳定,也使检察机关的办案人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不明真相的社会舆论也会将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误解为“放纵”犯罪。因此,对受害人情绪激动、舆情关注的案件,即使在审查逮捕时就知道法院可能判轻刑,但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权衡中,检察机关也不会轻易作出不捕决定。
[案例三]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于2012年10月11日10时许,在其所居住的村里因占地施工问题与同村的被害人葛某争执并揪扯,刘用匕首将葛胸部、腹部、大腿等处刺伤,致葛血气胸,经鉴定被害人葛某损伤为轻伤。案发后,由于刘某某和葛某为同村村民,两家因占地盖房有矛盾导致案件的发生,双方在打斗过程中,不仅被害人受伤,犯罪嫌疑人一方也有受伤,案发后,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多次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申诉,要求严惩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双方未达成调解的情况下作出了批准逮捕刘某某的决定。在本案移送法院后,双方家属进行了调解赔偿,被害人出具了谅解书,法院作出了拘役5个月的判决。
(四)办案质量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和检察实践发生偏差
实践中,以捕后判轻刑率考核权重加大为代表的审查逮捕质量总体考核分值加大,反映了上级检察机关对审查逮捕执法质量的高度重视,显示了其杜绝缺陷案件甚至错案的决心。对此,具体参加考核的检察人员深有体会,但考核方案刚刚实施,对考核的结果应用尚未显现,这就需要全体检察人员未雨绸缪,提早动手,统一思想,“防轻刑于未然”。在检察系统外部,对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考核及对审查逮捕工作的评价均对捕后判轻刑案件重视不够,基本不检查、不过问、不做评价。在审查逮捕工作的评价中,也不涉及此类案件。相反地,对不捕案件则要求层层备案、案件评查复查,决定程序复杂,年度还必须复查。长此以往,使检察人员形成了人为压低不捕率,忽视轻刑案件逮捕必要性论证的惯性思维。
(五)捕后证据发生变化导致最终被判处轻刑
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批捕、起诉证据标准不一,批捕后出现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导致轻判;另一种是刑事和解。刑事和解主要在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盗窃和寻衅滋事案中,有下述三种情形:(1)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初期、逮捕之前尚未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与达成和解对后续处理的影响,不愿意赔偿,但其一旦被逮捕,态度即发生转化,积极赔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法院认为对其不监禁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对其判处轻刑;(2)犯罪嫌疑人愿意赔偿并有一定的赔偿能力,但被害人漫天要价而达不成协议,把逮捕看成了要挟犯罪嫌疑人多赔钱的工具,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开始到批捕阶段时间有限,而从批捕到到审判阶段时间较为宽松,加上被害人的情绪逐渐稳定、期望值也有所降低,较容易与犯罪嫌疑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法院便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罚;(3)犯罪嫌疑人受经济条件所限确实无赔偿能力,而被害人在案发初期又不依不饶,就得先逮捕,但如犯罪嫌疑人确系真诚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院亦对其从轻处理。
(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认识不一致导致捕后判轻刑
虽然办案人员对法院的“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进行了充分的学习,但审查批捕部门毕竟不是审判机关,两机关在执法理念上存在差别:一是与法院在主体资格、事实证据、涉案罪名以及化解矛盾纠纷的认定上存在分歧。如对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法院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认为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就作为判轻刑的依据。长期以来,由于机构设置和工作性质的不同,法院在对待化解矛盾纠纷的认识和处置上相比于检察机关略胜一筹,检察机关对此相对较为谨慎,体现在审查逮捕的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严”字当头;二是个别审判机关过度适用罚金刑,以罚代刑,导致捕后轻刑率较高。
[案例四]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因与被害人张某某成为不正当男女关系后产生矛盾,韩某某纠集社会无业人员马某先后6次前往被害人店铺、家里及亲属家里,对被害人及其母亲等人采取砸门、威胁、辱骂并扬言进一步加害被害人亲属,情节特别恶劣,已严重地侵害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人身权利,公然破坏社会秩序,而法院在认定“二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后,即作出了对两被告人各判处拘役5个月的轻刑。
(七)相关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不健全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外来人口如何减少羁押没有相关的制度保障;二是在审查批准逮捕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理因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轻微犯罪中的从犯以及群体性事件中的一般参与者等时,如何贯彻从宽的刑事司法政策,如何落实社区矫治和帮教措施,相关配套法规相对滞后,工作机制不够健全。
三、降低捕后法院判决轻刑率的对策建议
保障诉讼是逮捕措施的首要价值。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中,一部分被法院最终判处轻刑,并不必然意味着适用逮捕措施的失当。但是,应把降低捕后判决轻刑率作为提高审查逮捕工作水平的途径,通过采取有力措施,有效解决因执法观念和工作机制问题导致的捕后判轻刑问题,以体现刑法“谦抑性”要求,在保障诉讼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出台类似人民法院“常见罪名量刑指导意见”的规范性文件,明确常见罪名“无逮捕必要”具体的适用范围、标准
在批捕阶段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司法理念,主要是对“无逮捕必要”的案件尽量不予批准逮捕。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对“有逮捕必要”条件规定了要考虑的因素,但只是指导性意见,没有具体形成规范,办案人员在办案中没有具体可执行的标准。因此,有必要对“无逮捕必要”的范围、条件加以明确,省级检察院可以比照各省高级法院从多发性、判轻刑较多的常见案件入手,结合各地法院判例实践,对盗窃、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案件进行具体的“无逮捕必要”量化规定:
宁波刑事律师,你身边的律师帮手,13605747856【微信同号】
继续阅读

我的微信
如果以上文章对你有帮助
扫一扫,加律师的微信,了解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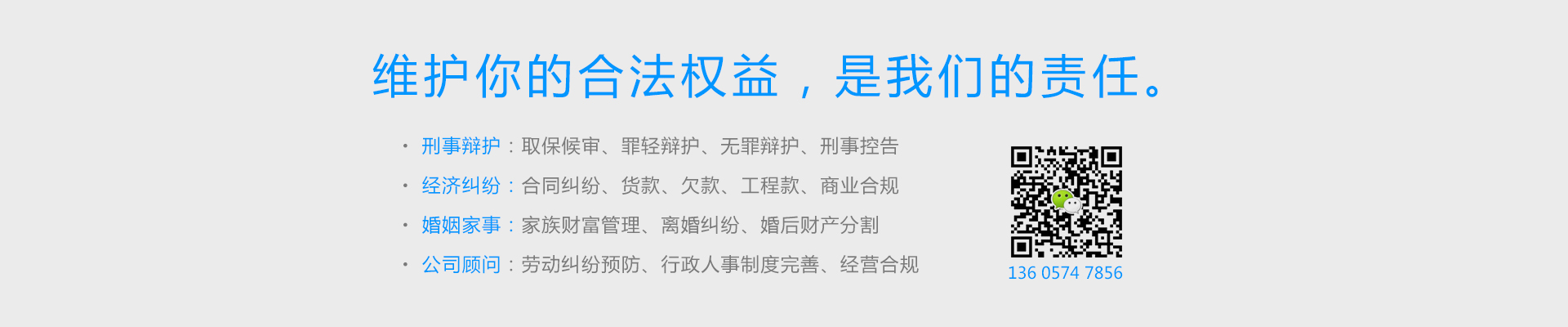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