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在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有一对衣冠齐整的男女做爱,但他们并没有脱去外衣,而且还刻意遮掩关键部位,既不让想他人发现,更不想让一丝春光暴露于外。这种情形如何认定?在法律上会处罚吗?
既然做爱是人性的一种本能,又是种族繁衍的必经手段,它为什么被“光天化日”所排斥,而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为什么,在公共场所的做爱,都不能被接受为那公共场所的秩序的一部分,而要被认定是“对秩序的扰乱”?
优衣库的视频被刷屏的时候,我应该在做梦。醒来时,伊已经被朝阳群众举报,了无痕了。
这时有人来电话,约我写一篇,可见都没见,哪来激情写。何况纸上得来终觉浅,那些真有激情的,都去试衣间里躬行去了,哪还会趴在办公室写一篇。
关键是不知道写啥。我以前都没听说过优衣库,只知道优酷。优酷搞了这么多年视频,现在优衣库一脱衣服,就比优酷出名了,不公平。
而且,世界那么大,人们见识过璩美凤、陈冠希、李宗佑等一批老一辈行为艺术家的巨星风采,谁还会对这点三里屯视频大惊小怪?
出乎我意料,这次好像有点不同了。通常模式是:朝阳区观众鉴定完视频后,一般要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鉴定完视频后,一般要从法律上追究其他区的观众。然后也就拉倒了。
但这次,除了视频传播者的责任之外,人们开始正经八百地讨论,那对视频中的男女,有没有法律上的责任?
原因是,与那些前辈在家里表演不同,优衣库影片的摄影棚,是一个在法律上界定起来有点困难的地方——试衣间。
很多人翻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现在问题来了:在试衣间里做爱,违法了吗?
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是微信上一个关于优衣库事件的采访。
受访律师认为,试衣间属于提供给顾客的服务场所,应当认定为公共场所,而且发生性关系比法律条文规定的裸露身体更严重,法律后果也应该更严重。
我在朋友圈里转发评论,“这都是在上学时没好好学习的”。类似这些稀里糊涂和稀泥的说法,看了也就是一笑而过。
再后来,看到朋友圈里有经济法和宪法的教授认真关心这事,他们坚定地认为,当事男女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试衣间不是公共场所。理由是,它可以被解释为广义的“住宅”。
这种苦心孤诣维护个体自由的老右派式的执着,让人感佩。但是,这个理由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在法律解释上,住宅一词的边界,必须受制于“住宅”在汉语中可能文义的射程。只有在这个边界之内,才能充分考虑具体空间的实际功能。
如果说解释工作是一场球赛,可能文义就是球场上的边裁。任何功能解释和目的解释,不管多能跑,翻跟头都行,但不能让球出界,否则,边裁就得吹哨,重新比赛。
至于说,一个词语的可能文义究竟是什么,只要解释者站在客观的立场,诉诸一般中国人的汉语语感,考虑日常交往中的语言习惯,并不难把握。
举个例子,《刑法》规定了倒卖车票船票罪,那倒卖飞机票的,能不能处罚?
无论两者作为运输合同凭证的功能多么相似,相信也不会有人赞成在汉语中把飞机票称作“车票”。正如“打车”和“打飞机”也是各有其意,绝不能混用一样。
同理,即使把“住宅”的日常用法推至弹性的边界,谁会带着相亲对象指着试衣间说,我有房,这就是我的“住宅”?——女方可能反手一巴掌,这还是老娘的爱呢。
解释者不得逾越可能文义的限度,因为那代表着立法的民主基础。无论对部门法还是宪法,都是一样。一旦超越,就进入了立法者的领域。
除非你是美国最高法院那五位大法官。连“婚姻”都能修改成包括同性的结合,对“住宅”进行无限解析更不在话下。——可惜,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制。违宪审查都不存在,还幻想对宪法用语进行篡改,死了这条心吧。
解释不进去,能不能类推适用呢?
不错,试衣间与住宅的空间,都是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但是,作为一个关键特征,住宅的核心功能是基本的生活起居,这无论如何也不好让试衣间承担。
如果真有人在试衣间里吃喝拉撒睡,要么会被认为是行为艺术家的表演,要么,这块地儿就不会再被人叫做“试衣间”了。
所以,将试衣间解释为“住宅”,或者在功能上类推适用住宅,试图以此来为当事人插上自由的翅膀,飞离“公共场所”的泥沼,恐怕是行不通的。
不是住宅,那试衣间就应当属于“公共场所”吗?
有人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是!
同时,公共场所也有规矩,也需要适当的限制,如公共厕所就有男女之别。试衣间只要里面没人谁都可以进去(试衣),不能因为里面有人时其他人不能进去就否定其公共性,更不能因为试衣时有可能暴露个人隐私就否定其公共性。在这种谁都可能进入或者接近的场合,发生男女鱼水之欢,显然比一般的‘故意裸露身体’更为恶劣。”
——金泽刚:“试衣间应是公共场所”,《新京报》2015年7月21日
这段铿锵有力的论述,出自一位刑法同行之手,直接把我震懵了。左思右想,竟不知如何评述。只想弱弱地问一句:
原来,这商场里的试衣间,竟是一座每个人都注定要沉沦其中的原罪陷阱。真是细思恐极。
挑刺儿很容易。困难的是正面阐述:试衣间到底是不是公共场所?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5处条文规定了“公共场所”,但是没有对公共场所做出一般性的定义,只是在第23条明确列举了“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这几处常见的公共场所。
按照体系解释的基本原理,其他法条中的“公共场所”,至少应当与这些明确列举的场所在性质和功能上相当,具有共性特征。
翻看人大法工委撰写的法律释义,给出的说法是,“公共场所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对公众开放,供不特定的多数人随时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
把这句话再向前推进一步,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只有一个在物理空间上可以“供不特定的多数人随时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才能承载人们的公共生活。
法律人之所以要讨论这样一个场所,正是因为人们通过这个场所进行社会活动,形成了一定的公共生活秩序。不是这个场所本身,而在这些场所中展现出来的公共生活,才是法律关心的对象。
所以,“公共场所”不是一个物理的、建筑的、空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法律的、文化的、规范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由水泥砖瓦组成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由一群人的社会生活交织而出的动态的秩序。
把握住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场所”背后的法律精神,而不至于脱离开法律的思考,僵化地通过新华字典解释“公共场所”这四个汉字。
例如,商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明确的“公共场所”。在大白天商场正常营业的时候,把尸体停放在人来人往的商场大厅,这行为无疑符合该法第65条规定的“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
但是,商场下班之后,深更半夜趁着商场里无人,同样是把尸体停放在商场大厅,天亮来人之前又运走,这种行为就不应当适用第65条。
在物理空间上,这都是同一个商场,但是下班之后,在空旷无人的商场之内,已经不存在任何由顾客往来形成的社会生活,也就失去了值得保护的公共秩序。
被抽离了公共秩序的场所,仅仅是一片冰冷的水泥森林,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壳,不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
“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但没有了人的生活,法律之眼就不再眷恋。
直到太阳升起,开门营业,第一个顾客走进来,这家商场才重新回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怀抱。
再如,公园和展览馆都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的“公共场所”。同样是跳广场舞,在公园里跳就没问题,但如果是在展览馆里跳,就可能构成第23条规定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同样一座殡仪馆,肯定不属于第65条规定的“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中的“公共场所”,但是,却可以认定为第44条“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中的“公共场所”。
相反,浴池和厕所肯定不属于第44条意义上的“公共场所”。进入这些场所,还故意不裸露身体的,可能反而有点问题。相反,对第65条而言,浴池和厕所当然属于“公共场所”,敢在这些场所停放尸体的,不处罚简直没天理。
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
相反,在展览馆里跳舞,在殡仪馆裸奔,在浴池停尸,那就与这些场所的社会生活和特定秩序格格不入,甚至会造成严重侵扰。将这些场所认定为相关法条中的“公共场所”,对侵犯秩序的行为进行惩罚,就是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适用。
其实,这些结论,仅凭朴素的法感情就能轻易获得。从法理上说,公众在不同场所进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是不同的,不同场所的特定功能存在差异,对应着各种具体而相异的公共秩序。
因此,在认定“公共场所”的时候,不能抽象地、泛泛地一概而论,而是必须结合相关法条的具体语境,廓清该法条中“公共场所”的特定功能和相应范围,结合在个案的具体场所中开展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来加以判断。
总结完毕,关于试衣间的问题,答案也基本出来了。
即使承认试衣间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它也不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意义上的“公共场所”。
理由很简单,试衣间是干嘛用的?试衣服的。换衣服的过程中,能完全避免身体(关键或敏感)部位不裸露吗?不能。如果能,谁还进试衣间呢。但凡进去的,就是怕走光——没见过买手套的,还专门进试衣间戴一下吧。多新鲜啊。
所以,试衣间的特定功能,就在于让进入其中的人,可以放心地裸露身体。如果一定要说试衣间也是公共场所,那么,这就是场所里应当受到保护的生活和秩序。
于是,试图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来处罚试衣间里的性爱,就遇到了下面的法律适用的悖论:
如果你反对上面的说法,质疑说,试衣间里的秩序只是为了正常的换衣服,男女做爱怎么能说是这秩序的一部分?那么,这就是认为,男女做爱不能被评价为“故意裸露身体”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试衣间里做爱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故意裸露身体”的要素,不能适用第44条。
所以,还是放过他们吧。
继续讨论。在试衣间到底是不是公共场所的问题上,其实还可以换一种思路。
当我们谈论“公共场所”与“私人空间”之别时,广场与住宅是最典型也最易理解的例子。
在人流穿梭的广场上,没有人能够支配自己周边的空间。眼看着一个厌恶的人从眼前走过,但你毫无办法,不能对他发出“此路是我开”的禁令,因为那空间是“公共场所”。
但是对自己住宅里的空间,人们有着绝对的支配力。你不仅可以让喜欢的人进来,更可以让不喜欢的人永远在门外。法律人最喜欢念的咒语就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那试衣间呢?它是更像广场,还是更像住宅?
每个人自从穿衣服开始,大概就没有没进过试衣间的。遍布在各大商场和各个街头小店的试衣间,是一种专门为买衣服的顾客试衣而设的空间。
这种空间通常不大,容纳1-2人而已,通过设置门锁或者门帘等障碍,与外界隔离开来。但它的奇特性在于,既不完全像住宅,也不完全像广场。
与住宅相似,又与广场不同的是,当你进入试衣间时,那里面的空间就归你支配。门锁或门帘的阻碍作用,不仅是事实上的,而且是规范上的——未经你许可,其他人不能也不允许进入这个空间。
但是,一旦你离开了试衣间,里面没人了,别的顾客就可以任意进去,并取得同你之前一样的支配权。这可不像住宅,即使家里空无一人,那也是你持续支配的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同意有的学者将试衣间解释成“住宅”的原因。它们不仅在日常语言的用法上难以相通,在人与空间的规范关系方面,也相去迥异。)
这样看来,进出试衣间人员的不特定性,以及空间的非独占性,倒又有点像广场了。
如果把广场理解为一种无人可独占和支配的空间,把住宅理解为一种归个人独占和支配的空间,那么,试衣间,就是一种介于广场与住宅之间的、神奇的空间。
它的神奇性在于,每个人一旦进入,就具有了一种独占和支配这空间的规范性魔力。而他一旦离开,这魔力旋即消失,又会被其他进入者获得。频繁换手的空间支配力,充满了暂时性与流动性,这就是试衣间既不同于公共场所,也不同于私人空间的独特之处。
有谁规定的真理说,这世界上的空间,只能区分为公共场所与私人空间两类?为什么一定要用人造概念来形成二元对立,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剪裁事物呢?
所以,不必陷入到试衣间“若非私人空间,就必然是公共场所”的泥沼里。你完全可以说,它两者都不是,所以找不到明确的法律禁令。
就这样。
让我们继续讨论吧。
说完了“公共场所”,再说说“故意裸露身体”。“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这条文虽然只有几个字,里面的世界却很大。
先说“身体”,肯定不是指人体的所有部位。否则,夏天穿短裙秀长腿的姑娘,以及在路边光膀子撸串的爷们,都可能被抓起来。
凭借朴素的法感情,人们会很容易说,“身体”应该是指那些敏感的身体部位,例如男女的生殖器。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尿急,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卫生间,于是跑到角落里脱裤子方便,这算不算“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
可能有人会说,当然算。公共场所的角落,那也是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还可能被人看见关键部位,多不讲道德。当然,也会有人认为不算,虽然有点不雅,毕竟也没对着谁尿吧。
哪一种说法对呢?
范伯格在讨论刑法的道德界限时认为,对一个明显(但不是极端的)的自由主义立场而言,可能不会接受将家长主义和道德主义作为惩罚根据,但至少会同意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
简言之,只有当一个行为损害或冒犯到他人时,才能为刑罚提供正当性基础。
假设这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设立处罚的正当性基础。那么,尿急时找个角落方便,并不是直接针对他人的损害或冒犯,也就不适用这一条。
可能有人反对说,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为立法宗旨、以拘留为最严厉手段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惩罚基础上应当比《刑法》更宽泛。
那就切换到保守一点的立场。在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之外,还接受道德主义作为惩罚根据,即一个行为虽然无害,但是会令公众在道德上反感的话,也能成为治安处罚的对象。
这样一来,在公共场所方便,就很可能由于具有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性质,而被评价为“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的行为。
于是,是否惩罚在公共场所方便的行为,就取决于,在这两种惩罚根据中,应当为第44条选择哪一种呢?
要做出适当的选择,还是要回到这个法条的前半段。
再看一下第44条规定的全貌,“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请注意:“猥亵他人”与“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被并列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中,共用一个法定惩罚力度。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与“猥亵他人”共享同一个惩罚根据和基础,它们的行为性质与危害性是相当的。
因此,惩罚“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的行为,仅仅因为不符合道德还是不够的,而应该如“猥亵他人”一样,必须具有在性方面损害或者冒犯他人的性质。
从这一点来说,尿急时在公共场所角落里方便,即使符合了“故意裸露身体”的形式,但那只是具有排泄的意味,并不包含性侵害或性冒犯的含义。
到此为止,我们逐渐看到了“故意裸露身体”的典型形象。那就是俗称的露阴癖,百度定义是:
除了生殖器以外,第44条中的“身体”,还包括其他能够传递性含义和性信息的“准性器官”。例如,臀部或女性的胸部(男性就算了)。面对他人裸露这些传递性信息的身体部位,都是针对他人的性冒犯。
现在,我们再回到优衣库事件。
从相关新闻报道的画面来看,当事男女是在试衣间里脱光了衣服做爱。做爱当然具有天经地义的性内涵。裸露的重点部位也打了马赛克。这样看来,认定为“故意裸露身体”,似乎并没什么疑问了。
但是,别忘了前面说过,仅仅是重点部位的裸露还是不够的,仅仅是行为本身具有性含义也不够,与“猥亵他人”相并列的“故意裸露身体”,必须具有在性方面损害或者冒犯他人的性质。
猥亵他人当然是直接的性侵害了。对着别人脱裤子的露阴癖,也当然是对他人的性冒犯。
但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试衣间里做爱,只有当事男女两人,其他人未经许可不能入内更无从得见,如果不是当事人自拍的视频流出,根本就无人得知试衣间里的风景,这样的行为,到底是直接性侵害或性冒犯了谁呢?
找不到答案的话,就只能得出结论说:
由于不存在针对他人的性侵犯或性冒犯,因此,试衣间里的性爱,不能被涵摄进(与“猥亵他人”相并列的)“故意裸露身体”的规定之中。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追问,如果当场就有其他顾客发现了试衣间里的异常,注意到里面的情况,因此感到非常尴尬和不适,这算不算是被冒犯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把我们的讨论又引向了深入。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或许由于试衣间的门帘不严,其他顾客看到了里面的裸身性爱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故意裸露身体”?
如上所述,要想在客观上符合第44条的“故意裸露身体”,仅有裸露是不够的,必须要求这种裸露行为具有向他人传递性含义和性信息的性质。而要满足这一点,至少要让他人看见其裸露的身体。
简言之,裸露,必须是面向他人的裸露。
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要认识到全部的客观行为。因此,只有在裸露者认识到自己是在面向他人裸露身体而仍为之时,“故意裸露身体”的主客观要件才算是齐备了。所以,如果试衣间的性爱被他人看到,但做爱者本人对此尚不知情时,就不属于“故意裸露身体”,不能适用第44条。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其他顾客没有看到,但是通过一些异常的声音,猜测到了试衣间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会感到尴尬和不适,这算不算是对他人的性冒犯,因此适用第44条呢?
回答依然是否定的。第44条规定的“故意裸露身体”,是指通过裸露的身体来传递性信息,使得他人因为看到其身体而被冒犯。这个规定的意思,并不是指裸露身体时造成了一些声音,再经由这些声音传递的性信息来冒犯他人。
那种通过声音来形成的冒犯,与法条规定的“裸露身体”没有涵摄关系,因此并不适用第44条。
问题来了:
当然有。
这种情形虽然不适用第44条,但是,却可能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在这种情形下,那个被扰乱了秩序的“公共场所”,不是试衣间,而是商场。当事人的行为性质,也不是“故意裸露身体”的问题,而是对商场营业秩序的“扰乱”。
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让我们先回到试衣间。想象一下它的构造。试衣间的门墙,围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将试衣者裹在其中,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为脱光了衣服的人,又披上一件可以遮羞的钢筋水泥的外衣。
现在,有没有发现两个例子的相似之处?在公园或地铁里穿衣做爱的人,他们身上穿的布质外衣,与试衣间的隔板外衣,本质上是一样的。在这个外衣的遮蔽之下,都有一对男女在裸身做爱。
因此,关于试衣间里做爱的各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在其他毫无争议的公共场所的做爱行为。
由于穿着外衣且刻意遮掩关键部位,所以不适用第44条的“故意裸露身体”(当然更不能认定为淫秽表演和聚众淫乱)。
但是,如果这种行为还是没能逃过朝阳群众法眼,那就没办法了,被他人当场发现和鉴定出来这事情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打破了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等公共场所的沉静的水面,没有能够成功地伪装成那秩序的一部分。不幸地暴露了。
情形类似的,还有车震。人们躲在自己的私家车里做爱,与躲在试衣间里做爱,或躲在自己衣服下做爱,本质上是一样的——只要这个作为遮羞布的汽车、试衣间和衣服,在整体上处在一个无可争议的公共场所。
在个案中需要考虑的仅仅是,这种做爱行为对公共场所的公共生活,扰乱到何种程度。例如,遮羞布的遮蔽程度(汽车和衣服的差异),公共场所的人流量(空旷无人的路边和人流如梭的车展的差异)。
这些差异决定了客观上的危害性,折射出主观上的放纵心理,因此,也当然地影响到裁量结果:是否需要动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以及,采取何种处罚措施,是一般的警告罚款足矣,还是需要拘留。
这结论,听起来有点让人唏嘘。男欢女爱,本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可那句歌词怎么唱的来着,“谁又能凭爱意 将富士山私有”。
到此,问题真的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
试衣间里做爱,是一个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也是一段看起来毫无争议的法条。它才11个字。
但是,一花一世界。在那个最简单的事实与法条之间,由于法律人的目光往返流转,也可能搭建起一座包罗万象、俯瞰众生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展开对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当然主要是法教义学和解释学的工作。但是,的确又不止于此。
例如,凭借法教义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和技巧,我们很容易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做出解释,然后坚决地得出“在试衣间里做爱不适用该条”的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出结论说,在各种公共场所做爱引起关注(包括在试衣间里做爱因制造声响而被关注),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时,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法教义学本身难以解决的犹豫。
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依靠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教义学分析本身,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一个解释者,内心对这个答案没有确信,他对第23条的解释和适用,就只能是一种“想来理应如此”的盲目和茫然。
不能简单地用违反“公序良俗”来回答。那相当于是重复包装了一遍问题。
也不能简单地用“被冒犯”来回答。因为会追问,为什么会被冒犯?如果围观者看得津津有味呢?
还不能简单地用违反道德来回答。这个时代的法律,已经有那么多条文显示出了对道德多元化的容忍,但为什么当众做爱就不行呢?
不是说这些回答不对,而是说,要让他人信服,至少要让自己内心确信,可能还不够。
但没人能给出唯一正解。
在解释和适用法律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遭遇困难和犹豫,指导他鼓起勇气继续运用技术得出结论的那些“内心确信”,往往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的人可能偏爱道德理论。性本身就是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具体的性实践,包括方式、频率、时间、场合,都不能任性而为,而是要接受道德原则的指引,这本来就是人与禽兽之别。
在朱熹眼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他举例,“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按此,做爱是天理,但是没有约束和克制的公开做爱,就是要灭除的人欲了。
有的人可能愿意经济分析,功能主义地考虑后果和效率。公开做爱的性实践,利润在哪里?处罚的成本与收益有多大,会带来什么后果,不处罚又会引起何种激励?
按波斯纳在《性与理性》里的说法,人们的厌恶,哪怕是非理性的,不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外部成本吗?
有的人可能喜欢从政治哲学上论证。公权力与个体自由的边界何在?国家能够或应当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标准和范本吗?就像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里的提问,“道袍的国家还是体现个人身体曲线的国家”?
有的人可能青睐身体政治学和治理术的分析。按照福柯的说法,“所有那些乌托邦,正是通过反对这个身体,才开始形成的。第一个乌托邦,在人们心中扎根最深的乌托邦,很有可能恰恰是一个无肉身的身体的乌托邦。”
如果说治理是通过身体的规训而引导人的灵魂,那么对身体性爱的限制,就是形成秩序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公开做爱,恰恰是身体本能的最大释放,具有冲破一切身体规训和蔑视各种秩序的破坏力。
1968年,巴黎学生在街头涂鸦,“越革命,越做爱;越做爱,越革命”。革命是秩序的天敌。在公共场所做爱,不仅仅是“扰乱”秩序,这种让秩序感到害怕的东西,已经是一种革命。
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一道“公共场所做爱是否违法”的题目背后,拷问的是每个法律人各自的人生经历、阅读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些内心确信。
它们如同脑海深处的潺潺流水,推动着我们的思维之舟,也滋润着每一个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技术动作,让法教义学的工作,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枯燥干涸。
只是,大江流日夜。谁又能保证,自己这脑海中的潺潺流水,在时间、历史和人生际遇的弯道起伏中,又会激起哪些意想不到的浪花呢。而那些浪花,也终究会影响到我们对法律的修正和理解。
那些封闭的条文和教义,永远不会束缚住法律人的想象力,那里有一个向着生活开放出无限可能的世界。
世界那么大,一起去看看吧。
宁波刑事律师,你身边的律师帮手,13605747856【微信同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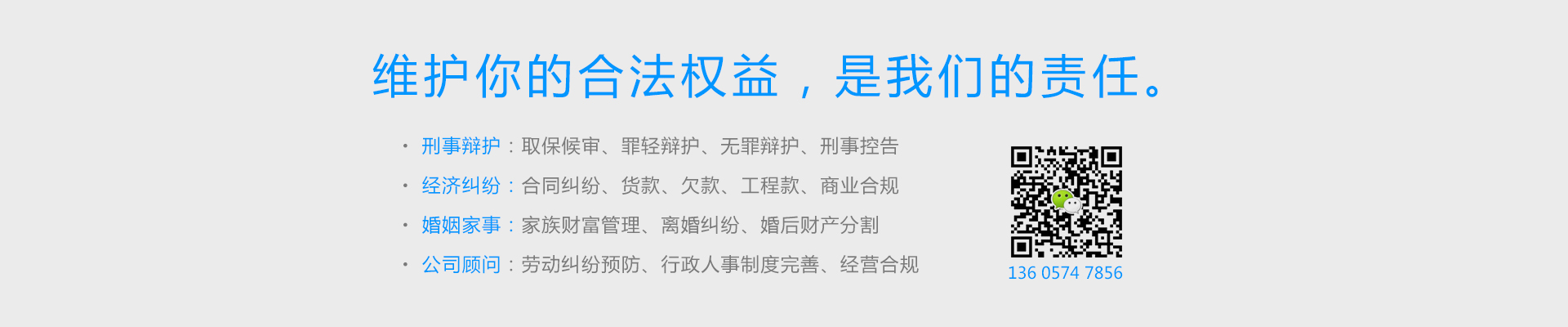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