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背离刑法的性质,导致刑法扩张、其他部门法不扬。造成刑法和其他部门法“角色定位”的混乱。(2)背离刑法的机能,强化社会保护而忽视人权保障。过度刑法化本身就是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作为犯罪进行惩罚,实质上是通过“合法的”形式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侵害。(3)背离刑法的功能,导致社会管理手段的弱化。过度刑法化导致刑法扩张、其他部门法萎缩,自然的结局就是其他部门法的预防制度和预防机制的匮乏,并最终导致社会管理手段的弱化。(4)注重刑法实用主义,导致刑法庸俗化,刑法成为随时都可以使用和适用的工具,工具主义思想泛滥,刑法威严扫地。
关键词:过度刑法化;刑法功能;刑事处罚早期化;预防刑法
今年是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第22年,我们单就以时间为轴、以数字为参考,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表现:(1)22年间我们通过了10个刑法修正案,大致每2年通过1个修正案;(2)刑法分则条文数量从350条增至373条,刑法分则条文的增加意味着罪名的绝对增加;(3)刑法罪名数量从1997年的412个增至469个。尽管不排除有根据社会发展必须进行犯罪化的情况,但客观上在这些新增的法条和罪名中,过度刑法化所占的比重较大。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中国刑法已经在过度刑法化的推动之下,从注重事后惩罚走向了注重事前干预。不仅在刑事立法层面存在过度刑法化,在刑事司法层面也有非常明显的过度刑法化的表现。
具体来讲,我们当下的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道德滑坡、刑法拉动。“道德滑坡、刑法拉动”在当下中国刑法的修正中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势头,除了《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虚假诉讼罪、考试作弊罪、使用虚假身份证罪等,刑法学界还一直在讨论“见危不救”“挥霍浪费”等行为的入罪。希望通过刑法对于不道德行为的惩罚,从而威慑人们不去实施不道德的行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泛道德化”。(2)民法不扬、刑法扩张。需要解释的是这里的民法并不是狭义的民法规范,而是代称除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从性质上来讲,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只有在其他部门法不能规制某种行为的情形下,才动用刑罚进行惩罚,这也是刑法的谦抑性之所在。但如果其他法律不能得到科学的修正和进化,势必将所有的社会纠纷推到刑法领域进行惩罚,于是就造成了今天“民法不扬、刑法扩张”的局面,而且使刑法具有“一再扩张”的张力。(3)理念转向、积极预防。刑法在以往也注重预防,但是彼时的刑法预防是通过对其他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惩罚从而实现预防,预防是惩罚犯罪的“副产品”,只是在注重特殊预防的同时,侧重于一般预防,而当下的刑法预防是“为了预防而预防”。混淆了刑法和行政法、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关系。(4)制度缺位、刑法补足。所谓制度缺位、刑法补足是指本来应当通过制度进行约束和规范的行为,但是我们缺乏对于制度的设计和建构,于是这种制度缺失导致的违规行为或违法行为,就由刑法完成相应的惩罚和预防职能。
随着社会发展和新型犯罪的出现,进行适当犯罪化是正当的,毕竟刑法就是应当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如果过度刑法化,将原本不应当犯罪化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认定为犯罪,一方面是对法律体系科学性的破坏,更重要的是对公民自由和权利造成侵害。过度犯罪化无疑是个严肃又严重的问题,国会应当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因为在过度犯罪化的情形下,任何的不公正就是对整个公正体系的巨大威胁。[1]美国学者从五个方面批判了他们的过度犯罪化:(1)过度犯罪化导致了犯罪问题上的过度联邦化,也即强化了国家的主权,在国家和州的利益上,优先考虑国家的利益;(2)过度犯罪化处罚了微不足道的行为,以及只是涉及个人道德的行为;(3)对于犯罪行为缺乏道德谴责和非难的基础;(4)过度犯罪化导致刑法扩张以及刑法典的臃肿;(5)过度犯罪化导致了重刑。[2]而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国情,中国的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隐忧主要表现以下为四个方面,文章将逐一进行论述。
对于刑法和其他部门法关系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又影响刑法侵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会影响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发达程度。因为,一旦刑法极度扩张,那么必然侵蚀原本属于民法、行政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部门的调控范围,从而出现“刑法扩张、其他部门法不扬”的局面。所以,如果刑法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和活动中表现得非常强势,那么,其他部门法就会有所保留,从而不再那么表现出张力,慢慢地就会培养和惯习出刑法的“飞扬跋扈”和“一支独大”。
Victor Tadros指出,只有能够产生某种效益的刑罚惩罚才是正当的,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刑罚惩罚必须能够减少犯罪。相应地,如果认定为犯罪并进行刑罚惩罚的效果并不明显和充分,民事制裁就应当优先。尽管民事制裁也是给犯罪人造成负担,但是民法的目标并不是让犯罪人承受痛苦。[3]
刑法应对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类型进行区分,从而使违法行为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第一类违法行为遵循“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的原则,让这些违法行为不进入法律的系统之内。第二类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被害人正式而又完全的自主权,由被害人决定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还是授权给检察官通过刑事诉讼途径解决。第三类违法行为,被害人就不再拥有自主决定权,检察官可以在有或没有被害人授权的情形下提起刑事诉讼。[4]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法律体系中的各个法律部门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尽管说刑法可能会和部分部门法的规制范围发生一定的重合,但还是能够对彼此的规制界点和范围有一个明晰的划分。
所以,在一国法律体系区分刑法和民法的理由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刑法在形成社会规范和对人民行为进行规范过程中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明显。与其他实体法相比,在新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原有法律规范的强化加固过程中,刑法承担了非常重要和核心的作用,而且刑法能够在短期内获得直接的尊重。但刑法直接和广泛影响社会的功能的发挥需要具备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刑法的规定和内容应当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也即是应当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5]
民法和刑法的最大差异就是刑法惩罚的犯罪行为代表了人们对犯罪行为的谴责,而民法的制裁措施并不包含对行为的谴责,无论是违反合同的行为还是侵权行为都没有对违法行为人的谴责。而人们都具有非常强烈和普遍的道德评判的渴望,那么我们在建构社会评价系统时终究需要建构这样一个子系统来实现人们进行道德评判的渴望。而独立的刑事司法系统就是唯一有效的让人们表达对犯罪行为进行谴责的方式。[6]
但是,现在刑法和民法的界限有模糊和混乱的趋势。民法承担了部分刑法的功能和角色,比如增加了对人身伤害的赔偿;但是更多的是刑法大幅度扩张到民法领域,包括传统的民法中的违法行为。利用刑法惩罚违反行政法的情形一直在增加。而且刑法在处罚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时经常使用严格责任和替代责任,刑法大幅度扩张的一个结果就是增设了大量并不包含道德非难和谴责的刑事犯罪。[7]
相反,通过民法手段实现对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控制却具有较长的历史。民法手段实现犯罪控制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第一,民法制裁手段,比如赔偿、恢复原状和道歉,可以直接融合到刑事司法过程中,从而取代监禁刑和其他刑事惩罚措施;第二,许多原本通过刑罚进行惩罚和规制的行为,现在可以通过可选择的民事制裁实现,比如未成年人法庭和地方法庭,在这些法庭中,可以存在更广阔的治疗和谈判的空间,解决纠纷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充满对抗,而且可以让被害人参与到诉讼过程之中;第三,在决定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过程中,比如非法持有少量的大麻,多是利用警告和罚款,而不是通过刑事惩罚;第四,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通过行政法(包括当地政府规章和命令)许可程序来制止或抵御某些行为,设立特定的政府部门来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这些措施的目标就是减少能够纳入到刑事司法系统笼罩之下的反社会行为、危害行为和犯罪行为。有些犯罪行为通过民法途径解决是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比如未成年人犯罪;有些是为了避免刑事诉讼上的证明的困难,比如对公司犯罪和白领犯罪,通过刑法惩罚公司犯罪和白领犯罪时,在证明个人的可谴责性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困难。所以,有些国家通过行政、经济和民事制裁来控制公司犯罪。[8]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刑法客观上具有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但是不应当将这种功能无限地扩大,而且不应当忽视了刑法功能发挥的最后性和补充性。罗宾逊教授指出,一个国家的刑法具有三个层面的功能:第一,刑法被用来宣告某些行为构成犯罪,通过宣告某些行为构成犯罪并进行惩罚,从而让社会公众按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第二,如果某人的行为违反刑法的某条规定,通过刑法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第三,刑事司法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将犯罪人的责任落实为具体的刑罚。[9]其中第一种功能,罗宾逊教授称之为Ex Ante Function,笔者理解应当是我们刑法中所称的一般预防。具体的含义就是刑法典划定了合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刑事司法强化了社会公众对于这种罪与非罪界限的认识,社会公众基于对于刑罚的恐惧,以及认可了法律系统所强化的道德价值,从而不愿意跨越犯罪的界限。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民众事实上是否认识到有这种界线的存在呢?[10]因此,为了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我们工作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立法和从重从严的刑事司法,而是立法机关应当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让民众明白刑法的内容,明白允许的行为和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这是立法机关的一项责任,而不能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之后,法律效果的好坏完全交给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这是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和客观规律的。
但是,我们现在秉承的思路是一味强化刑法的威慑效果和预防效果,让刑法的威慑效果和一般预防效果无限扩大和放大,无视其他部门法和道德规范对社会公众行为规范的引导作用。这也就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外刑法理论中都在讨论的预防理论家族的第三支后裔:积极一般预防理论。该理论深信以刑罚来确认与强化公民对规范忠诚的价值信念。其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和目的就是,通过刑事司法的运作对公民产生社会教育所激发的学习效果,从而让公民形成见到法律受到贯彻时所产生的信赖效果。[11]当刑法将自己的使命定性为确认和强化人们对于规范的认同,就等于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可以随时指手画脚的长者地位,如此就容易干涉原本通过其他部门法便可以解决的纠纷。
尽管都是以“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为出发点,但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却在不同的理念支配下,可能会呈现出三种图景:(1)先后关系。也即是在规范公众的行为和处理社会纠纷时,其他部门法在先,刑法在后,只有在其他部门法不能规范和惩罚相应的行为时,才动用刑法进行预防和惩罚;(2)并列关系。也即是其他部门法和刑法都具有引导公众行为规范和惩罚违法行为的功能,二者同时发挥作用,只不过其他部门法规范轻微的违法行为,刑法惩罚严重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3)颠倒的“先后关系”。也即是在规范公众行为和处理社会纠纷时,刑法优先,其他部门法滞后,强化和扩大刑法的威慑作用。秉承这种思想的潜意识就是:既然刑法和其他部门法都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刑法的效果又较为明显和直接,为何选择效果“缓慢”的其他部门法而不直接选择效果“短平快”的刑法?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刑法对于整个社会管理活动和领域的全面涉入,包括家庭领域、道德领域等等。这就促生了我们国家当下的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而弱化了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不能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公共安全作为首要任务,而为了实现公共安全的保护,国家和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战略和新的规制工具。根据克劳福德的统计,在多数西方国家和地区“新的规制工具组合”就是弱化传统的法律和命令,在惩罚和规制体系中给予刑法一个更大的框架和空间。[12]强化刑法在规范人们行为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中的功能和角色,势必就会弱化和漠视其他部门法的功能,从而导致刑法的一再扩张和其他部门法的持续萎缩。
对于刑法机能,通说认为是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二元机能,尽管也有学者认为除了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之外,还具有行为规制或行为规范机能。但刑法最为基本的机能就是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并且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应当得到同等对待,不能厚此薄彼。因为,刑法从本质上讲其不仅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如果社会公众基于内心认同而尊重法律,很显然刑法功能发挥就好;相反,如果社会公众基于强制和被迫而遵守法律,那么刑法功能的发挥显然会大打折扣,而且会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但是在实际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我们往往会为了表现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重视,同时,也为了满足公众对某些行为的愤怒情绪,重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而忽视其人权保障机能。
刑法修正案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扩张刑法进而实现对社会的保护:(1)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张,主要表现就是直接增设罪名;(2)刑事处罚时间的提前,实现刑事处罚早期化,主要表现就是预备行为、准备行为犯罪化;(3)刑事处罚标准降低,主要表现就是入罪数额或情节标准降低。可以说这三种模式都注重刑法对于危害社会行为的预防,刑法呈现非常明显的预防性特征,而且这种预防性刑法的趋势还在加剧。我们当下的刑法已经从注重事后惩罚转向了事前预防,而不考虑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危害的可能性以及时间的紧迫性。比如,我们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将刑事处罚的起点一再前移,实施刑事处罚早期化。
犯罪前预防(pre-crime)最早出现于1956年菲利普·迪克的科幻小说《少数派报告》,犯罪前预防本来是一个“特别警察小组”的称号,他们的职责是依据三个具有预见未知的先知的预见,在犯罪发生之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踪和逮捕。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得恐怖袭击成为犯罪前预防的试金石。针对恐怖袭击的先发制人战略落实到刑法中就是犯罪前预防,将刑法的重点从事后的惩罚转向对于具有潜在危险的人员的识别和在危险转化为实害之前的介入和干预。[13]但是,令人充满兴趣和不安的是,建立在风险评估程序和推测想象基础之上的预防犯罪措施的程度究竟如何确定?[14]正如《少数派报告》中反映的一样,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先知预测的准确性。如果先知预测错误,我们有何种救济措施?同时,我们还需要准确找到预防犯罪的犯罪前时空(pre-criminal space),犯罪前时空包括犯罪人本人实施的行为,也包括对犯罪人的行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行为。[15]《少数派报告》作为艺术作品的科幻小说本身已经指出了预防犯罪存在法理上的缺陷,存在侵犯无辜民众自由和人权的无限可能。贯彻李斯特的特殊预防理论,其结果往往会抛弃责任原则以及事实原则。为了以具有可持续的方式预防犯罪,最好不要等待犯罪发生,而是应当对危险个体事先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正是刑事立法对打击恐怖主义正在做的事情。[16]
预备行为、犯罪参与行为与实行行为相比,在应受谴责程度上具有类型化的差异,除非有特殊的刑事政策需要,不宜将这种原则性的差异做立法上的消除。《刑法修正案(九)》的上述立法选择显然没有在立法合理性层面上作深入的考量。[17]有人提出过度犯罪化的一个原因是针对国家的恐怖主义,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国家必须做出应对,而刑法是其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种回答可以解释为了收集证据而放松对证据收集的要求(比如电子监控),或者允许执法机构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合作。但是却不能解释国会对于国内的情形(比如针对安然公司)和舆论事件(劫车事件)而增设刑事犯罪的原因。而且,必须说明的是,不能将过度刑法化完全归咎于2001年9.11的恐怖分子,因为在此之前,过度犯罪化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与恐怖主义没有关系。[18]基于刑事处罚早期化,我们增设了预防风险的罪名,而为了实现对于风险的预测,我们采取了诸多预防和监控措施。我们能看到也切身感受到的就是各种监控设备的存在,在公共交通枢纽中的宽严程度不等的各种安检,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公民个人信息(身份证)的查验,在公共道路上的基于各种理由停车检查(查醉驾、超载),等等。这些预防性刑法措施客观上确实能够起到预防犯罪和发现犯罪的功能,但其对公民自由的压缩和侵犯也非常明显。而且,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预防性刑法措施预防犯罪的效果是不明确的,但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却是现实的和明显的。
同时,对于预防性措施效果的衡量机制也有利于推动该措施的实施。通常来讲几乎没有相应的机制和措施来衡量它们的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广泛使用拦停搜查的措施、FBI将一些线人或代理人送到穆斯林群体之中、要求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人进行“特殊的登记”、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将某些人划入禁飞或二次筛选、财政部门冻结某些人的账户、国家安全局监控几乎每一个美国人的电话,等等,这些预防性措施并没有在法庭上呈现。即便有一些预防性措施被报道出来,也是作为正面的报道强调其取得实际效果。但是,如果民众知道对83000多人的特殊登记只是为了搜查一名恐怖分子,人们就会考量预防性措施的正当性以及是否值得这样做?[19]尽管我们不应当弱化或扩大预防性刑法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新的规制措施和先发制人控制机制与规范公众行为的牵强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制工具和措施具有适用于我们社会中最容易受攻击的群体的可能性。[20]
有论者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进行了分析,该论者指出,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每增加一个刑事犯罪的边际效用可能为零,但是边际成本却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如果我们认为每增加一个刑事犯罪就是对我们的公众福利的一种削减,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增加刑事犯罪。我们完全可以只依靠现有既定数量的刑事犯罪,但是我们可以对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人员变量提出要求(包括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等),以及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设备变量提出要求(包括计算机、法庭数量、通讯设备等)。[21]尽管说刑事犯罪和社会治理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运作,但这种思路告诉我们,完全可以从社会治理的人、财、物以及制度设计的层面探索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惩罚,可以探索通过非刑事手段实现社会治理。
对于刑法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最为经典的论述可能就是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意思就是我们通过科学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设计,可以避免多种犯罪的发生。一方面可以避免新型犯罪的出现,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犯罪量的增加。该论断证明了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社会政策的“治本”特性,也间接说明了刑法的“治标”本性,以及在社会治理问题上,刑法功能的有限性。
刑法的机能和刑法功能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本质上相差甚远。刑法功能具有属人性,它根据适用主体对刑法的需求和希望发挥的作用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刑法的机能不具有属人性,只是刑法客观上所具有的机能和机理。刑法功能的属人性决定了其具有主观性和变动性;刑法机能的内在性决定了其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所以,对刑法功能的分析和界定,我们需要明白是站在何种立场和角度。是路人的立场,还是具有某种法律知识和素养的专业人士的立场,还是被法律思维标准腐蚀的司法人员的立场?站在不同的立场,可能刑法功能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22]如果该国认为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刑法功能就会进行相对的限缩。相反,如果认为刑法应当是社会治理的工具,那么,刑法就会承担原本应当是社会制度和其他社会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所应当承担的功能。
而我们当下的社会治理生态是原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属于被动启动的刑法,现在却具有非常强烈的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冲动,对于许多违法行为,我们并没有进行制度设计,也没有给予制度试错的机会和时间,直接通过刑法进行预防和惩罚,但这种刑法过度干预的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对于腐败犯罪,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刑罚措施,也不论我们采取多么严重的刑罚惩罚,腐败犯罪肯定是存在的。这一方面证明了刑罚效果的有限性,同时也说明在腐败犯罪预防问题上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且预防腐败最好的方式应当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就是说通过制度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约束,防止利用权力进行寻租。
比如,危险驾驶原本就是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但是基于“维护社会公众出行安全和交通安全”,将危险驾驶行为认定为犯罪,最高刑期为拘役6个月,这种处理客观上并不能完全有效遏制危险驾驶罪。而对危险驾驶罪,我们并不能实现对所有的危险驾驶行为和危险驾驶人员犯罪化,那么就会导致被抓获的犯罪人员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多么可耻和值得谴责,而是认为自己“倒霉”和不够聪明,如此一来,刑法的威慑效果可以说大打折扣。如果实施某种行为并构成犯罪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和值得谴责的,那么这种犯罪的一般预防效果就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制定了相应的预防醉酒驾驶和危险驾驶罪的制度,这样醉酒驾驶的人员从内心认为自己是在违反相应的制度,从内心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和可谴责的。
美国过度犯罪化的表现有四大标志:(1)扩大严格责任在刑事犯罪认定中的适用,尤其是商业领域和行政管理领域;(2)能够同时适用多种法律的行为,也就是多个法律竞合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不接受辩诉交易,那么检察官就会威胁行为人构成犯罪并被监禁;(3)授权行政机关行使填充和解释刑事实体法要件的权力,行政机关拥有解释刑法细节的“马甲”,就会让他们从执行法律转变为解释法律;(4)原本应当由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管理或民法机制解决的行为,而通过刑事犯罪进行实施。[23]这四个过度犯罪化的表现在中国的过度犯罪化中也都能找到对应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过度刑法化的表现就是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机关的权力,将原本应当通过行政监管的行为转处为通过刑法进行惩罚。行政监管行为表现出较为明显实质刑法化特征,从而导致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
比如,为了规制在医疗健康过程中日益突出的“过度医疗”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修正了已经实施150多年的“民事欺诈请求法”,以便起诉那些在医疗过程中被认为实施了无效的、过于昂贵的和没有必要的医疗行为的人。而对医生过度医疗行为的惩罚,一方面会让原本随着社会发展而自然进化的医疗技术冻结和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有可能产生政府规定的定量配额。同时,对于此类犯罪是否处罚,可能完全取决于检察官在决定惩罚对象以及严厉程度方面的自由裁量权。[24]
有论者就指出,美国国会应当控制持续的行政犯的增加。因为,行政机关一贯性制定规则并越过国会将某些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实际上,通过新的行政条款和行政监管进行犯罪化的机制已经形成。有人估计在美国大约有30万种行政违法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这种趋势导致了刑事犯罪的一种新的演化过程,同时也对刑事犯罪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国会不应当再将这种权力下放给行政机关。[25]
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也非常得明显和突出,监管机关可以通过监管法规或规章降低“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的标准,包括数额、情节、严重程度等等,将原本违反行政法规、规章、制度的行为转为刑事犯罪。比如枪支的认定标准,发生在天津的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让这一问题呈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现有的公安机关认定枪支的标准是:枪口的比动能大于1.8焦耳。如果行政机关对枪支比动能标准进行调整,客观上就是在调整刑事犯罪圈。如果将比动能标准提高,很显然许多人的行为不再构成涉枪犯罪;相反,将枪支的比动能标准降低,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原本是生产、销售、购买玩具枪的也构成相应的枪支犯罪。
我们在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选择中,选择了犯罪化,那么就意味着刑法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刑法在我们当下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更高、权重更大。刑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过大,其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而且深远的,较为直接后果就是将会导致治理手段的弱化。
因为,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并没有探究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的动力,而是非常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于公众的犯罪意念和行为,从而将其认定为犯罪,并自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但实际上导致问题发生的根本症结并没有找到,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过度犯罪化导致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但是过度犯罪化导致的一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过度犯罪化是摆在国会面前诸多集体行为问题的原因或症状(cause and symptom)。[26]换句话说就是,将某一行为犯罪化昭示着我们在制度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解决此种行为的能力短缺。
我们把社会治理过程中稍有困难的问题都归结为犯罪人的违反法律的主观心理,从而将他们作为犯罪人进行惩罚,定罪判刑送进监狱之后,所有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便得到了掩盖。这一点在责任事故中便显得最为明显。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责任事故,最直接的安抚措施就是将数名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认定为犯罪人进行惩罚,公众愤怒的情绪得到了平复。但是真正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没有找到。而且,被行政问责的官员经过一点时间的潜伏可以再次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有可能在其再次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后,重特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故依然发生。于是,相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再次被追究行政责任,如此反复。这就是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制度安排的原因的结果。
我们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包括死刑、包括终身监禁,但是依然有人“前腐后继”。这就是没有从根源上找到遏制腐败发生的制度和机制,所以无法避免和减少腐败的发生。对于违法行为,应当注重从根源上寻找原因,并积极探究解决的方法,构建制度和机制,从制度层面和机制层面遏制此类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再次发生。比如对电信诈骗罪,单纯地通过诈骗罪进行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预防,但是银行系统内部将通过银行卡转账和提现的时间延长的规定,就从治理层面上有利于犯罪的预防。
刑法作为宪法之下的部门法之一,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是无可厚非的,但刑法的实用性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而不能将刑法实用性庸俗化为社会治理的工具。遗憾的是,在刑法万能论的思想推动之下,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庸俗化特征。笔者认为,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刑法修正呈现出“无下限”和“无上限”的特征。所谓“无下限”是指无论什么行为,只要社会公众有所呼吁,立法机构就有将其犯罪化的冲动,缺乏对拟犯罪化行为的危害性及入罪后的刑罚设置和立法效果等问题的全面衡量和评估。所谓“无上限”是指通过“刑法修正案”可以修正刑法中的所有问题,并不受宪法和立法法所确定的立法权限的制约。不仅可以随意修正刑法分则增设罪名,还可以修正刑法总则设定刑罚制度。比如对死刑制度的修正,对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提高,社区矫正的设定,终身监禁的确立,等等。可以说,这些刑法制度的修正都涉及全体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而且已经触及到刑法的根基,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修正,而我们却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改的。
这就导致了原本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能修正的法律,现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修正。这样一方面违背立法权限的规定,另一方面有违刑法保护利益的普遍性和公允性,不能对相关的修正内容进行系统、充分、全面的讨论,容易被部门利益所推动和挟持,从而随意地处理。比如,尽管《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终身监禁”,但是由于对其在进入刑法典之前缺乏系统的研究,从而导致目前为止,学界对于终身监禁的定性,其究竟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还是刑种,究竟是死刑替代措施,还是死刑执行方式;终身监禁期间是否能够保外就医等问题存在争论。笔者认为这就是将刑法实用性庸俗化和随意化的后果,而刑法修正的随意性和便捷性会加剧社会治理主体、社会公众等对于刑法实用主义的追求。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出发点就是追求刑法能够解决现实中问题的实用主义。而在注重刑法实用主义观念的推动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会更为突出和明显。可以说“469个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一点也不夸张。如此就会导致刑法的庸俗化。所谓刑法庸俗化,笔者也称之为刑法的随意化、恣意化,也即是司法人员可以非常随意地出入人罪,并不会完全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这一方面有司法人员司法良知的问题,也有司法人员重定罪、重刑罚的职业倾向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立法给刑事司法的随意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之争和西方国家的纯粹的二元机能之争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刑法的功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混乱。在今日的中国法治环境中,刑法更多地如同是一个消防队员,哪里有火情,哪里就有消防队员;而哪里有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哪里就有刑法介入的身影。尽管1997年刑法第三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经过一定时间的宣传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影响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但是由于我们立法技术的科学性欠缺和司法活动无限的艺术性,导致刑事司法活动过度犯罪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从而侵蚀了刑法的权威性,使刑法一步一步走向庸俗化。
比如,在中国刑法中能够规制“致人死亡”的罪名就有这么几个: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交通肇事罪、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滥用职权罪,等等。我们可以想,如果通过某种行为导致他人死亡,那么完全可以通过上述罪名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尤其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其现在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口袋罪。可以说只要有致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本罪。因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者“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应当预见”和“已经预见”从性质上都是规范判断要素,而不是事实判断要素。既然是规范要素,那么判断标准就完全取决于判断主体的主观认知。判断主体认为“应当预见”、“可以预见”,那么行为主体就有责任;判断主体认为“没有预见”、“不应当预见”,那么行为人就没有责任。
刑法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三个词:犯罪、羞愧(谴责)和整合羞愧。整合羞愧是整合理论的核心概念,根据该理论,如果社会能够有效地将犯罪认定为是值得谴责的,那么就会实现较好的犯罪控制,能够实现较低的犯罪率。相反,如果某种犯罪行为被认为并不让人感到羞愧而且不应当被谴责的,那么就会有较多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比如说,如果强奸是男人们炫耀的资本,那么强奸罪的犯罪率就会比较高。[27]
基于实用主义出发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往往容易受到短期内发生的多个典型案件的视觉冲击,并且容易被媒体的集中报道所左右,从而偏离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基于平复公众情绪的目的而将某种行为在立法或司法中认定为犯罪。将这些行为犯罪化的过程往往并没有经历如同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的较长时间历史的检验,不能让公众对行为的危害性和可谴责性形成共识,犯罪的反伦理基础较为薄弱。当对特定案件的讨论和舆论消退之后,公众往往对相应行为的刑法处理有所反思。比如,当风险社会的概念刚进入中国之后,刑法学界开启了对风险刑法的讨论,并在风险刑法的基础上推动增设了部分犯罪,调整了部分犯罪的处罚时间和处罚界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人们又开始了对风险刑法的反思。风险刑法理论在对刑法例证的论证中,过于大而化之而没有细致推敲,结果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有这些,都使得风险刑法理论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28]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出罪和入罪并不是一线之隔,而是一念之差。不是基于罪与非罪的界限来进行入罪和出罪,而是基于立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一念之差来进行判断。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出现非常明显的“不拿刑法当刑法”的思想,对待刑法的严肃、严谨的认识不复存在。刑法呈现出非常庸俗和实用的形象,但凡社会中出现问题,可以随时使用刑法进行预防和惩罚。这种过度实用和随意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正在一步一步瓦解公众自古形成的对刑法的尊重和畏惧的心理和传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促使社会对刑法的畏惧情结消解,而社会对刑法畏惧的消解又会再次催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如此恶性循环,将会彻底导致刑法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局面。
中国人自古就有崇尚刑法的内心情结,但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随意化、庸俗化、过度实用化让公众崇尚刑法的内在情结正在消解。反而使公众逐渐地不再信任刑事司法、不再相信法律是为了实现对犯罪的惩罚。在法律大家庭的谱系中,刑法呈现的应当是一种威严的面孔。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最终刑法“备而不用”的愿景,才能达到“刑期于无刑”的目标。换句话说,应当让刑法供奉在法律的神坛上,而不能经常让刑法走下神坛。如果刑法走下神坛,那么刑法的威慑力和一般预防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而立法中频繁增加罪名、司法中过度能动化,运用刑法对相应的行为进行惩罚,将会背离刑法的性质,促使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混同,不能体现刑罚特有的威慑力,导致刑法的普遍化和庸俗化,刑法的严肃性、严厉性荡然无存。
【注释】王强军,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罚处罚早期化的限制与理论应对研究”(18BFX106);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及其限制研究”(AS17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发表于《当代法学》 2019年第2期。
[1]Paul J. Larkin, Jr.,“The Extent of America Overcriminalization Problem”,Legal Memorandum 121(2014).
[2]Roger A. Fairfax, Jr.,“From‘Overcrimializaiton’to‘Smart on Crim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Reform—Legal and Prospects”,17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Policy 609(2011).
[3]Vera Bergelson, “Book review: The Boundaries of the Criminal Law”,7 Crim Law and Philos 385(2013).
[4]Y. K. Lee, “Public Wrongs and the Criminal Law Ambrose”,9 Crim Law and Philos 160(2015).
[5]Paul H. Robinson, “The Criminal-Civil Distinction and the Utility of Desert”,76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14(2005).
[6]Paul H. Robinson, supra note [5],pp.201-214.
[7]Paul H. Robinson, supra note [5],pp.201-214.
[8]Sharyn L. RoachAnleu, “The Role of Civil Sanctions in Social Control: A Socio-Legal Examination”,9 Crime Prevention Studies 22(1998).
[9]Paul H. Robinson, Natasha R. Goldstein, Peter D. Greene, “Making Criminal Codes Functional: A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de of Adjudication”,186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1996).
[10]J. M. Darley, P. H. Robinson, “Ex Ante Fun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35 Law & Society Review 165(2010).
[11][德]米夏埃尔·帕夫利克:《目的与体系:古典哲学基础上的德国刑法学新思考》,赵书鸿等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页。
[12]StefaanPleysier, “Local Governance of Safety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Behavior”,64 Crime Law Social Change 308(2015).
[13]L. Zedner, “Pre-crime and Post-criminology?”,11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61-281(2007).
[14]Gabe Mythen, Sandra Walklate, “Pre-crime, Regul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Interrogating Anticipatory Risk”,81 Criminal Justice Matters 34(2010).
[15]David Goldberg, Sushrut Jadhav, Tarek Younis, “Prevent: What Is Pre-criminal Space?”,http://pb.rcpsych.org/content/early/2016/12/01/pb.bp.116.054585#BIBL, last visited on 20 December 2018.
[16]前引[11],[德]米夏埃尔·帕夫利克书,第220页。
[17]参见王志远:《〈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控制策略视野评判》,《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29页。
[18]Paul J. Larkin,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Over criminalization”,36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731(2013).
[19]David Cole, “The Difference Prevention Makes: Regulating Preventive Justice”,9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516(2015).
[20]StefaanPleysier, supra note [12],p.315.
[21]Paul J. Larkin, supra note [18],p.722.
[22]George P. Fletcher,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riminal Theory”,88 Californian Law Review 694(2000).
[23]Paul J. Larkin, Jr.,“Overcriminalization: The Legislative Side of the Problem”,December 13,2011,https://www.heritage.org/crime-and-justice/report/overcriminalization-the-legislative-side-the-problem, last visited on 27 December 2018.
[24]Isaac D. Buck, “Enforcement Overdose: Health Care Fraud Regulation in an Era of Overcriminalization and Overtreatment”,74 Maryland Law Review 260(2014).
[25]Dick Thornburgh, “Over criminalization: Sacrificing the Rule of Law in Pursuit of‘Justice’”,heritage lectures, No.1180,Delivered October 6,2010,p.5.
[26]Paul J. Larkin, supra note [23].
[27]John Braithwaite, “Shame and Criminal Justice”,42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81(2000).
[28]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103页。
关注该公众号
宁波刑事律师,你身边的律师帮手,13605747856【微信同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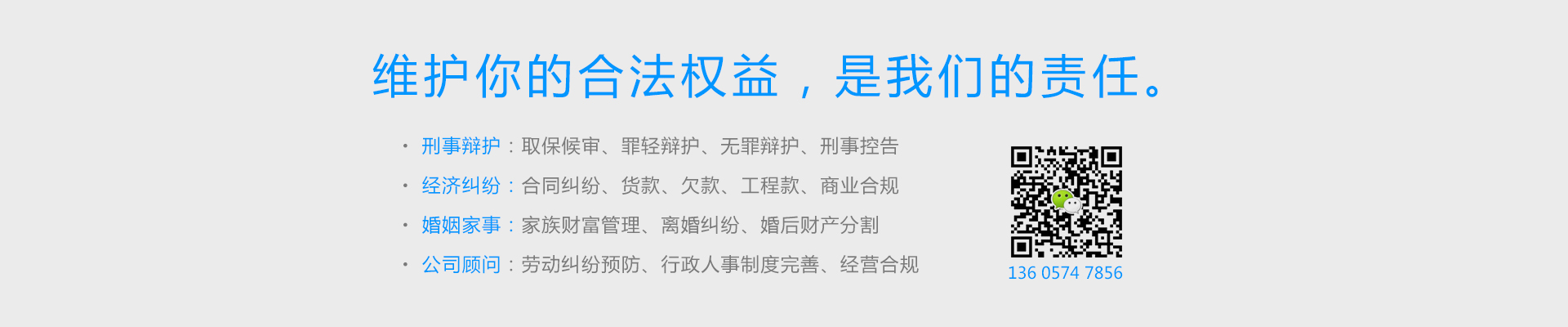

评论